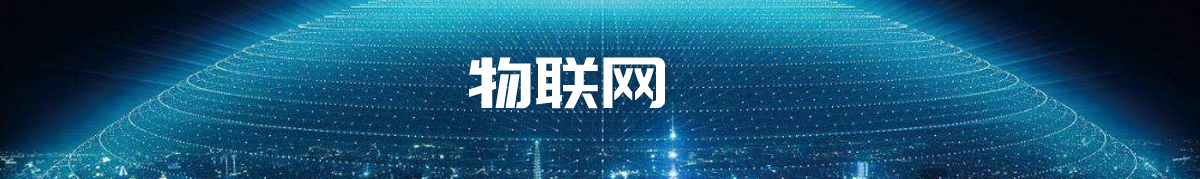藩国王安忆我追求繁华梦破灭
编者按:那是属于上海的废墟,上海夜夜笙歌,歌声是带着形式般迫不得以带欢庆的热闹,却是没有高山流水纯粹清澈,在这废墟里,袅袅娜娜的浮出一个清新雅致的影子,那是王琦瑶,那也是王安忆。
王安忆
一.作家简介:
王安忆,当代作家。原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移居上海。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母亲作家茹志鹃,父亲剧作家王啸平,自幼受母亲影响很深。
上海,是王安忆母女童年和成长的所在地。这样的地缘关系比血缘关系更加深刻地铭刻在王安忆的写作之中。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次年随母迁到上海, 1970年到淮北农村插队落户,1972年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回上海,任《儿童时代》。在王安忆的童年记忆里,由于干部家庭的特殊身份和语言的隔膜,初到上海这个大城市,她无法和外人沟通,找不到应有的伙伴。 “我的生活 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吧,我的性格是比较孤僻的,或者说就是蛮胆怯的吧,它使我损失了最早的进入集体的机会 就是进幼儿园。”在家里,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专注于写作,姐姐上学不在家,王安忆体会不到多少家庭的温暖。在喧嚣城市角落里,王安忆的童年是安静的。友情和亲情缺失让记忆充满了孤单,这些生命中最初的情感体会,深深影响了她人格成长和她的写作生涯,奠定了她的小说忧郁的基调。
童年的寂寞和保姆的和谐关系才让王安忆这个非上海本地人有更多机会去观察上海保姆所隶属的小市民阶级的生活,也更加喜欢关注普通人的平凡生活。王安忆自己也说“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看的人,也可能是我经常生活在一种很孤独的状态,无法参与,只能看,看变成一种生活。”童年养成的观察习惯,也为她后来从事写作带来了巨大的优势,使得她可以用细腻,真实的语言在作品中详细地勾勒出各种场景下的上海市民生活。
王安忆说:上海与其小说创作有着密切关系。她两岁时随母亲茹志娟南下,住进上海市中心典型的弄堂。附近就是淮海路和原震旦女子学院(现为上海社科院)。因此,对于王安忆,最初的弄堂道路是复杂又有序;生活是高尚、宁静而又十分平凡。同一弄堂里的居民十分复杂,既有像她这样的南下干部家庭,也有上海资本家的仆役。复杂的居住环境使王安忆从小就对人有特别的兴趣,而在所有的人中“市民”阶层又是她最熟悉也最感兴趣的。
二.代表作品:
王安忆,以文笔细腻缜密见长。 1977年发表作品,迄今出版《王安忆自选集》六卷,长篇小说《黄河故道人》《69届初中生》《流水三十章》《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短篇小说集《小鲍庄》《尾声》《我爱比尔》《隐居的时代》《忧伤的年代》《三恋》《妹头》,短篇小说集《王安忆短篇小说集》《剃度》,散文集 《独语》《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我读我看他们都为顾客准备了详细贴心的FAQ呢!》《寻找上海》,论著《故事和讲故事》《重建象牙塔》《心灵世界》等共五百万字, 部分作品有英、德、荷、法、日、韩等译本。《本次列车终点》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流逝》《小鲍庄》获全国中篇小说奖,《叔叔的故事》获首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二等奖,《文革轶事》《我爱比尔》分别获得第二届、第三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三等奖,《长恨歌》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少年王安忆
三.上海弄堂里的背影王安忆眼中的上海
王安忆与张爱玲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同样生长在上海,深得上海的灵气,也深谙海派的精髓,同为女性,深知女人的处境,对女性生命都有独到的观察和思考,她们作品的魅力吸引了海内外众多读者。有人认为王安忆是张爱玲的传人,是张派作品的延续。在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家均选择了一个城市作为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活动的场所,都市成为现代文化下一个有代表意义的社会景观,一个有典型意义的时代表征。她们的小说创作在表现都市与女性的题材上都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关注都市生活,都将视域放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显示出鲜明的市民立场和女性关怀意识。但是细读作品,不难发现,二者虽同为女性,同样生长在上海,但二者作品却各有各的特点,生活的顿悟、情感的理解和城市的印象各有不同。
有人把王安忆与张爱玲作比较,其实她们有许多不同:张爱玲是非常虚无的人,所以她必须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老房子、亲人、日常生活的触动。张爱玲知道只有抓住这些才不会使自己坠入虚无,才不会孤独。王安忆则不一样,她在生活和虚无中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方式。上海在王安亿的笔下是一条飘着生活气息的小巷的回忆,是庞杂弄堂里道不尽的沧桑,是各种各样脸谱的众生相,还有渗入空气中的一种叫“氛围”的抽象物体。将五彩人生演绎成一种无形的理性范畴之中。她的情感范围要比张爱玲深广,她一直往前走,即使前面是虚无,她也要走过去看一看,她不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满足。
王安忆寂寞独行的探索,她对文学时尚、媒体喧嚣冷静断然的处置方式,都让读者既钦佩又捉摸不定,钦佩她的才气,她的探索勇气,她对严肃文学的执著;捉摸不定的是她的傲气,她的拒绝热闹的姿态,她不轻易接受采访的冷然。
在根据王安忆去年于香港岭南大学所做的一次演讲整理出来的文字稿《张爱玲之于我》中,她谈到了自己对张爱玲的阅读感受,并特别比较了自己与张爱玲的异同
第一个不同是我和她的世界观不一样,张爱玲是冷眼看世界,我是热眼看世界。张爱玲是一种不太能变通的性格,我比她好商量,比她乐观。其次,张爱玲比较勇敢,她敢于往最虚无看,而我比较软弱,不愿意把事情推到那么极端的地步,我希望自己能处身得舒服一些。再有一点区别,我和张爱玲毕竟在不同的背景下生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对我来讲是个虚拟的时间段,对张爱玲却有着切肤之痛。
大家把我和张爱玲扯到一起,一般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我们都写上海。这十来年里,上海成为一个话题,成为一种时尚。在这种气氛的渲染下,我的《长恨歌》就被别人注意了,我和张爱玲在这里会合了。第二,我和张爱玲都是写实主义的。我们对日常生活和生活的表象都有兴趣。我追求的写作理想是和张爱玲有点接近的。第三点是我后来发现的,我和张爱玲喜欢同一个人的小说,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这里面又有点缘吧,也可以归根结底为同是写实主义的趣味。
1.《长恨歌》
长《长恨歌》以四十年代上海“沪上淑媛”王琦瑶四十年来的情爱经历为线索,记述了她如何演绎了一曲饱含长恨的悲凉之歌……我们的人生也不过如此。带着心平气和后的推心置腹,没有承诺,没有誓言,也没有结果,但情真意切,清声细语,娓娓道来,但不缺乏奇迹、辉煌和荣耀。平淡的生活中总有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是回忆中的繁荣点滴,是人生里的华丽底色。
上海的弄堂
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暗看上去几乎是波涛汹涌,几乎要将那几点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它是有体积的,而点和线却是浮在面上的,是为划分这个体积而存在的,是文章里标点一类的东西,断行断句的。那暗是像深渊一样,扔一座山下去,也悄无声息地沉了底。那暗里还像是藏着许多礁石,一不小心就会翻了船的。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作底铺陈开。一铺便是几十年。如今,什么都好像旧了似的,一点一点露出了真迹。晨曦一点一点亮起,灯光一点一点熄灭。先是有薄薄的雾,光是平直的光,勾出轮廓,细工笔似的。最先跳出来的是老式弄堂房顶的老虎天窗,它们在晨雾里有一种精致乖巧的模样,那木框窗扇是细雕细作的;那屋披上的瓦是细工细排的;窗台上花盆里的月季花也是细心细养的。然后晒台也出来了,有隔夜的衣衫,滞着不动的,像画上的衣衫;晒台矮墙上的水泥脱落了,露出锈红色的砖,也像是画上的,一笔一画都清晰的。再接着,山墙上裂纹也现出了,还有点点绿苔,有触手的凉意似的。第一缕阳光是在山墙上的,这是很美的图画,几乎是绚烂的,又有些荒凉;是新鲜的,又是有年头的。这时候,弄底的水泥地还在晨雾里头,后弄要比前弄的雾更重一些。新式里弄的铁栏杆的阳台上也有了阳光,在落地的长窗上折出了反光。这是比较锐利的一笔,带有揭开帷幕,划开夜与昼的意思。雾终被阳光驱散了,什么都加重了颜色,绿苔原来是黑的,窗框的木头也是发黑的,阳台的黑铁栏杆却是生了黄锈,山墙的裂缝里倒长出绿色的草,飞在天空里的白鸽成了灰鸽。
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其实它们是万变不离其宗,形变神不变的,它们倒过来倒过去最终说的还是那一桩事,千人千面,又万众一心的。那种石库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和一堵墙上。一旦开门进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出现在了头顶。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那二楼的临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上海东区的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门是镂空雕花的矮铁门,楼上有探身的窗还不够,还要做出站脚的阳台,为的是好看街市的风景。院里的夹竹桃伸出墙外来,锁不住的春色的样子。但骨子里头却还是防范的,后门的锁是德国造的弹簧锁,底楼的窗是有铁栅栏的,矮铁门上有着尖锐的角,天井是围在房中央,一副进得来出不去的样子。西区的公寓弄堂是严加防范的,房间都是成套,一扇门关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墙是隔音的墙,鸡犬声不相闻的。房子和房子是隔着宽阔地,老死不相见的。但这防范也是民主的防范,欧美风格的,保护的是做人的自由,其实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拦不住的。那种棚户的杂弄倒是全面敞开的样子,牛毛毡的屋顶是漏雨的,板壁墙是不遮风的,门窗是关不严的。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是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然微弱,却是稠密,一锅粥似的。它们还像是大河一般有着无数的支流,又像是大树一样,枝枝杈杈数也数不清。它们阡陌纵横,是一张大。它们表面上是袒露的,实际上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黄昏时分,鸽群盘桓在上海的空中,寻找着各自的巢。屋脊连绵起伏,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样子。站在制高点上,它们全都连成一片,无边无际的,东南西北有些分不清。它们还是如水漫流,见缝就钻,看上去有些乱,实际上却是错落有致的。它们又辽阔又密实,有些像农人散播然后丰收的麦田,还有些像原始森林,自生自灭。它们实在是极其美丽的景象。
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的;窗边的后门,是供大 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前边大门虽是不常开,开了就是有大事情,是专为贵客走动,贴了婚丧嫁娶的告示的。它总是有一点按捺不住的兴奋,跃跃然的,有点絮叨的。晒台和阳台,还有窗畔,都留着些窃窃私语,夜间的敲门声也是此起彼落。还是要站一个制高点,再找一个好角度:弄堂里横七竖八晾衣竿上的衣物,带着点私情的味道;花盆里栽的凤仙花、宝石花和青葱青蒜,也是私情的性质;屋顶上空着的鸽笼,是一颗空着的心;碎了和乱了的瓦片,也是心和身子的象征。那沟壑般的弄底,有的是水泥铺的,有的是石卵拼的。水泥铺的到底有些隔心隔肺的,石卵路则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两种弄底的脚步声也是两种。前种是清脆响亮的,后种却是吃进去,闷在肚里的;前种说的是客套,后种是肺腑之言,两种都不是官面文章,都是每日里免不了要说的家常话。上海的后弄更是要钻进人心里去的样子,那里的路面是饰着裂纹的,阴沟是溢水的,水上浮着鱼鳞片和老菜叶的,还有灶间的油烟气的。这里是有些脏兮兮,不整洁的,最深最深的那种隐私也裸露出来的,有点不那么规矩的。因此,它便显得有些阴沉。太阳是在午后三点的时候才照进来,不一会儿就夕阳西下了。这一点阳光反给它罩上一层暧昧的色彩,墙是黄黄的,面上的粗砺都凸现起来,沙沙的一层。窗玻璃也是黄的,有着污迹,看上去有一些花的。这时候的阳光是照久了,有些压不住的疲累的,将最后一些沉底的光都迸出来照耀,那光里便有了许多沉积物似的,是黏稠滞重,也是有些不干净的。鸽群是在前边飞的,后弄里飞着的是夕照里的一些尘埃,野猫也是在这里出没的。这是深入肌肤,已经谈不上是亲是近,反有些起腻,暗地里生畏的,却是有一股噬骨的感动。
上海的流言
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气有时是东西厢房的黄衣草气味,有时是樟脑丸气味,还有时是肉砧板上的气味。它不是那种板烟和雪茄的气味,也不是六六粉和敌敌畏的气味。它不是那种阳刚凛冽的气味,而是带有些阴柔委婉的,是女人家的气味。是闺阁和厨房的混淆的气味,有点脂粉香,有点油烟味,还有点汗气的。流言还都有些云遮雾罩,影影绰绰,是哈了气的窗玻璃,也是蒙了灰尘的窗玻璃。这城市的弄堂有多少,流言就有多少,是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的。这些流言有一种蔓延的洞染的作用,它们会把一些正传也变成流言一般暧昧的东西,于是,什么是正传,什么是流言,便有些分不清。流言是真假难辨的,它们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也是一个分不清。它们难免有着荒诞不经的面目,这荒诞也是女人家短见识的荒诞,带着些少见多怪,还有些幻觉的。它们在弄堂这种地方,从一扇后门传进另一扇后门,转眼间便全世界皆知了。它们就好像一种无声的电波,在城市的上空交叉穿行;它们还好像是无形的浮云,笼罩着城市,渐渐酿成一场是非的雨。这雨也不是什么倾盆的雨,而是那黄梅天里的雨,虽然不暴烈,却是连空气都湿透的。因此,这流言是不能小视的,它有着细密绵软的形态,很是纠缠的。上海每一条弄堂里,都有着这样是非的空气。西区高尚的公寓弄堂里,这空气也是高朗的,比较爽身,比较明澈,就像秋日的天,天高云淡的;再下来些的新式弄堂里,这空气便要混浊一些,也要波动一些,就像风一样,吹来吹去;更低一筹的石窟门老式弄堂里的是非空气,就又不是风了,而是回潮天里的水汽,四处可见污迹的;到了棚户的老弄,就是大雾天里的雾,不是雾开日出的雾,而浓雾作雨的雾,弥弥漫漫,五步开外就不见人的。但无论哪一种弄堂,这空气都是渗透的,无处不在。它们可说是上海弄堂的精神性质的东西。上海的弄堂如果能够说话,说出来的就一定是流言。它们是上海弄堂的思想,昼里夜里都在传播。上海弄堂如果有梦的话,那梦,也就是流言。
流言总是鄙陋的。它有着粗俗的内心,它难免是自甘下贱的。它是阴沟里的水,被人使用过,污染过的。它是理不直气不壮,只能背地里窃窃喳喳的那种。它是没有感,不承担后果的,所以它便有些随心所欲,如水漫流。它均是经不起推敲,也没人有心去推敲的。它有些像言语的垃圾,不过,垃圾里有时也可淘出真货色的。它们是那些正经话的作了废的边角料,老黄叶片,米里边的稗子。它们往往有着不怎么正经的面目,坏事多,好事少,不干净,是个膀鹏货。它们其实是用最下等的材料制造出来的,这种下等材料,连上海西区公寓里的 都免不了堆积了一些的。但也唯独这些下等的见不得人的材料里,会有一些真东西。这些真东西是体面后头的东西,它们是说给自己也不敢听的,于是就拿来,制作流言了。要说流言的好,便也就在这真里面了。这真却有着假的面目;是在假里做真的,虚里做实,总有些改头换面,声东击西似的。这真里是有点做人的胆子的,是不怕丢脸的胆子,放着人不做却去做鬼的胆子,唱反调的胆子。这胆子里头则有着一些哀意了。这哀意是不遂心不称愿的哀,有些气在里面的,哀是哀,心却是好高骛远的,唯因这好高骛远,才带来了失落的哀意。因此,这哀意也是粗鄙的哀意,不是唐诗宋词式的,而是街头切口的一种。这哀意便可见出了重量,它是沉痛的,是哀意的积淀物,不是水面上的风花雪月。流言其实都是沉底的东西,不是手淘万洗,百炼千锤的,而是本来就有,后来也有,洗不净,炼不精的,是做人的一点韧,打断骨头连着筋,打碎牙齿咽下肚,死皮赖脸的那点韧。流言难免是虚张声势,危言耸听,鬼鬼祟祟一起来,它们闻风而动,随风而去,摸不到头,抓不到尾。然而,这城市里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的。无论这城市的外表有多华美,心却是一颗粗鄙的心,那心是寄在流言里的,流言是寄在上海的弄堂里的。这东方巴黎遍布远东的神奇传说,剥开壳看,其实就是流言的芯子。就好像珍珠的芯子,其实是粗糙的沙粒,流言就是这颗沙粒一样的东西。
上海的闺阁
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闺阁通常是做在偏厢房或是亭子间里,总是背阴的窗,拉着花窗帘。拉开窗帘,便可看见后排房子的前客堂里,人家的先生和太太,还有人家院子里的夹竹桃。这闺阁实在是很不严密的。隔墙的亭子间里,抑或就住着一个洋行里的实习生,或者失业的大学生,甚至刚出道的 。那后弄堂,又是个藏污纳垢的场所。老妈子的村话,包车夫的俚语,还有那隔壁大学生的狐朋狗友一日三回地来, 的小姊妹也三日一回地来。夜半时分,那几扇后门的动静格外的清晰,好像马上就跳出个什么轶事来似的。就说那对面人家的前客堂里的先生太太,做的是夫妻的样子,说不准却是一对狗男女,不见日就有打上门来的,碎玻璃碎碗一片响。还怕的是弄底里有一户大人家,再有个 ,读的中西女中一类的好学校,黑漆大门里有私家轿车进去出来,圣诞节,生日有派推的钢琴声响起来,一样的女儿家,却是两种闺阁,便由不得怨艾之心生起,欲望之心也生起。这两种心可说是闺阁生活的大忌,祸根一样的东西,本勤花蕊一样纯洁娇嫩的闺阁,却做在这等嘈杂混淆的地方,能有什么样遭际呢?
月光在花窗帘上的影,总是温存美丽的。逢到无云的夜,那月光会将屋里映得通明。这通明不是白日里那种无遮无拦的通明,而是蒙了一层纱的,婆婆婆婆的通明。墙纸上的百合花,被面上的金丝草,全都像用细笔描画过的,清楚得不能再清楚。隐隐约约的,好像有留声机的声音传来,像是唱的周被的 四季调 。无论是多么嘈杂混淆的地方,闺阁总还是宁静的。卫生香燃到一半,那一半已经成灰尘;自鸣钟十二响只听了六响,那一半已经入梦。梦这将促进智慧滨海建设的加速落地。也是无言无语的梦。在后弄的黑洞洞的窗户里,不知哪个就嵌着这样纯洁无瑕的梦,这就像尘嚣之上的一片浮云,恍饶而短命,却又不知自己的命短,还是一夜复一夜的。绣花绷上的针脚,书页上的字,都是细细密密,一行复一行,写的都是心事。心事也是无声无息的心事,被月光浸透了的,格外的醒目,又格外的含蓄,不知从何说起的样子。那月亮西去,将明未明,最黑漆漆的一刻里,梦和心事都惬息了,晨曦亮起,便雁过无痕了。这是万籁俱寂的夜晚里的一点活跃,活跃也是雅致的活跃,温柔似水的活跃。也是尘嚣上的一片云。早晨的揭开的花窗帘后面的半扇窗户,有一股等待的表情,似乎是酝酿了一夜的等待。窗玻璃是连个斑点也没有的。屋子里连个人影都没有的,却满满的都是等待。等待也是无名无由的等待,到头总是空的样子。到头总是空却也是无怨又无良。这是骚动不安闻鸡起舞的早晨唯一的一个束手待毙。无依无靠的,无求无助的,却是满怀热望。这热望是无果的花,而其他的全是无花的果。这是上海弄堂里的一点冰清玉洁。屋顶*放着少年的鸽子,闺阁里收着女儿的心。照进窗户的阳光已是西下的阳光,唱着悼歌似的,还是最后关头的倾说、这也是热火朝天的午后里仅有的一点无可奈何。这点无可奈何是带有一些古意的,有点诗词弦管的意境,是可供吟哦的,可是有谁来听呢?它连个浮云都不是,浮云会化风化雨,它却只能化成一阵烟,风一吹就散,无影无踪。上海弄堂里的闺阁,说不好就成了海市蜃楼,流光溢彩的天上人间,却转瞬即逝。
上海的女儿
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这情态是有一些优美的,它不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的。它比较谦虚,比较温暖,虽有些造作,也是努力讨好的用心,可以接受的。它是不够大方和高尚,但本也不打算谱写史诗,小情小调更可人心意,是过日子的情态。它是可以你来我往,但也不可随便轻薄的。它有点缺少见识,却是通情达理的。它有点小心眼儿,小心眼儿要比大道理有趣的。它还有点耍手腕,也是有趣的,是人间常态上稍加点装饰。它难免有些村俗,却已经过文明的淘洗。它的浮华且是有实用作底的。弄堂墙上的绰绰月影,写的是王琦瑶的名字;夹竹桃的粉红落花,写的是王琦瑶的名字;纱窗帘后头的婆婆灯光,写的是王琦瑶的名字;那时不时窜出一声的苏州腔的柔糯的沪语,念的也是王琦瑶的名字。叫卖桂花粥的梆子敲起来了,好像是给王琦瑶的夜晚数更;三层阁里吃包饭的文艺青年,在写献给王琦瑶的新诗;露水打湿了梧桐树,是王琦瑶的泪痕;出去私会的娘姨悄悄溜进了后门,王琦瑶的梦却已不知做到了什么地方。上海弄堂因有了王琦瑶的缘故,才有了情味,这情味有点像是从日常生计的间隙中迸出的,墙缝里的开黄花的草似的,是稍不留意遗漏下来的,无。已插柳的意思。这情味却好像会泪染和化解,像那种苔熊类的植物,沿了墙壁蔓延滋长,风餐露饮,也是个满眼绿,又是星火燎原的意思。其间那一股挣扎与不屈,则有着无法消除的痛楚。上海弄堂因为了这情味,便有了痛楚,这痛楚的名字,也叫王琦瑶。上海弄堂里,偶尔会有一面墙上,积满了郁郁葱葱的爬山虎,爬山虎是那些垂垂老矣的情味,是情味中的长寿者。它们的长寿也是长痛不息,上面写满的是时间、时间的字样,日积月累的光阴的残骸,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这是长痛不息的王琦瑶。
解读
旧上海是繁华与糜烂的共存,被誉为“东方的巴黎”,但流于表面的繁华只属于上流社会,而且是华丽的一层外袍,是不接地气的空中楼阁。旧上海生活的“芯子”则是上海市民阶层的弄堂。
上海的弄堂就好比是北京的胡同,是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它是由连排的石库门建筑所构成的,并与石库门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多少年来,大多数上海人就是在这些狭窄的弄堂里度过了日久天长的生活,并且创造了形形 风情独具的弄堂文化。都说弄堂是最反映上海风情的建筑,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也对其有多处描写,弄堂对于老上海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民居形式,更是提供更加亲切生活的场所。弄堂里,每到夜晚来临时,人们就搬出摇椅、草席、竹榻放在自家弄堂门口,怡然自得的坐在那里乘起凉来,顽皮的小孩子们则是在弄堂之间追逐打闹,寻找乐趣。只要是弄堂中发生的一切,无论是什么咸酸苦辣、嬉笑怒骂的故事,都会感到特别的亲切与自然。
如果说弄堂里流泻出的点点滴滴是小家碧玉的细细索索,那上海女人就是里弄长巷深处的无声叹息。上海女人的悲凉情怀,在王琦瑶身上得到了最真切的体现。是上海的浮华造就了王琦瑶,又正是上海的浮华让这个女人走向毁灭。我们说上海是一座繁华的大都市,这种繁华作家如何将它体现出来?繁华背后的落寞又如何体现?就是通过上海女人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来体现。所以,王琦瑶,只是一个拿上台面的模板,她的经历再曲折再坎坷,都是合理的。在小说中“王琦瑶“一开始就是一个群体 上海女人的代名词,因为撇去她的经历,她的生活、她的姿态一如当时上海的许许多多人。 精打细算的聪敏,拿捏分寸的清高,对情感的敏感窥探,都是我们可以从书中切实感受到的。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旧梦彻底破碎了,有鸽子飞翔过天空的弄堂生活继续,但是,王琦瑶的“长恨歌”之后,再无一个王琦瑶,也再无一个王琦瑶的旧上海。
2.《天香》
王安忆的创作《天香》依然把目光聚焦在上海,但这个上海不再有现代上海的繁华和当代上海的喧嚣,而是在“上海”形成之前,那个在时光深处充满手工农耕时代市井闲情的“小上海”。写作《天香》的缘起在于上海地方掌故里一种叫做“顾绣”的地方特产,这种在史料中并无太多笔墨介绍的技艺,却借由晚明时期一个上海士绅家族的兴衰历史,呈现出迷人的遐想空间。
自洪武三年,开科取士,士子如同久旱逢雨露。尤其江南地方,多有殷实富庶人家,却不大有来历,读了书无非用作愤世嫉俗,抑或吟风咏月,总之自家消遣。一旦洞开天地,前程在望,无不跃跃欲试。于是,学校林立,人才辈出,到此时,可说鼎盛。那些大小园子,就是证明。每到春暖,这边草长,那边莺飞,遍地都是花开,景象十分繁荣。
此地临海,江水携泥沙冲击而下,逐成陆地平原,因此而称上海。南北东西河密布,多少年多少代,总苦于淤塞,无数沟渠成了平地,舟船断路,又有无数平地犁成沟渠,人家淹涝。每逢潮汛,泥泽交织,再倒灌进海水,好比在盐卤中浆一遍。历朝历代,无不忙于开河与疏浚。及至本朝,拓宽一条范家浜,与旧河黄浦,南跄浦合成申江,直向海口去。又疏浚咸塘港、虬江、北沙港、蒲汇塘、吴淞江、顾浦、大瓦浦……一并归向申江,奔腾人海,一个混沌世界终分出经纬来。嘉靖年,申江两岸设了六处官渡,天堑便有了通途。
嘉靖年还有一桩德政,就是筑城。三十二这一年,四至六月之间,就有五次倭寇从海上来犯,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官绅上奏朝廷,恳请筑城,得允之后,知府立即下令,募捐集资,划界制图。一时间,拆屋献田,倾家助役。十月动工,十二月便拔地而起城池。说及时真及时,仅一个月过后,倭寇就来,碰了个钉子,悻悻然而去。三十五年,卷土重来,足足围城十七日,到底也没有得手。三十七年,崇福道院重修,立碑记抗倭事迹。自此,上海平靖。
解读
《天香》中,王安忆笔下的上海,遥远又切近,贴切又陌生,对王安忆而言,小说虽然是虚构,可它是在假定的真实性下发生,虽然年代久远,却是十足的海派风格。王安忆的创作《天香》依然把目光聚焦在上海,但这个上海不再有现代上海的繁华和当代上海的喧嚣,而是在“上海”形成之前,那个在时光深处充满手工农耕时代市井闲情的“小上海”。写作《天香》的缘起在于上海地方掌故里一种叫做“顾绣”的地方特产,这种在史料中并无太多笔墨介绍的技艺,却借由晚明时期一个上海士绅家族的兴衰历史,呈现出迷人的遐想空间。
.《富萍》
《富萍》是继刚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之后的新作,讲述的是上海中层和底层的人们如何汇入上海,又如何在这座城市表像的浮华下聚集起来的故事。王安忆写的并非是富萍的故事,而是这座城市的故事。人,只是城市的景而已。敏锐的观察力和敏捷的才思使得她的笔力可以渗透到场景之中的任何细微之处。写一条弄堂,她能从位于石库门、新东区和旧西区弄堂的形形种种,写到弄堂前门后窗阳台晒台的结构功用以及屋顶弄底路面的感性特征,及至弄堂房顶老虎天窗精雕细琢的窗扇、细工细排的屋瓦,再到晒台矮墙上脱落的水泥,外露的锈红色的砖以及山墙上的裂缝,裂缝里倒长的绿色的草。
在他们居住的这片棚户的东南面,有一个水上运输大队的文化站。据说,早些年,这里是个有名的扬剧戏院。最早的淮扬大班,就在这里演出请神戏。有些老人们,还能记得起名角,也是班主潘喜云的样子。行头特别壮丽,艳红的盘身大蟒,宝蓝、鸭黄,翠绿的令旗大靠。大锣大鼓通天敲响,戏台四周香火摇曳,真是痛快淋漓。现在,这戏院成了个礼堂。开会,做报告,放电影,偶尔也会有外地不知名的小剧团来演出。平时,却冷清得很,只留一个退休的老船工看门。这里的小孩大都认识他,叫他公公。下了学,跑到这里,叫一声公公,公公就放他们进去玩了。进去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就是地方大,空空的一个院子,地上新铺了水泥。原先铺地的石板,撬起了。有一些,还堆在院墙底下。那礼堂也修过了,外墙上涂了水泥。门前两根立柱,原来是木头的,现在换成了水泥。只是底下两个柱子墩还是木头的,残留着一些斑驳的红漆。场子里也是水泥地面,长条凳都推在两边,一条搭一条地垒起,一直垒到齐窗户。窗户开得很高,扁扁的一排,有些像澡堂的气窗。那戏台并不大,大约,宽有十数步,深则七、八步。台两侧各有一根立柱,倒还是木柱,颜色也褪得差不多了。戏台的木头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板缝里就挤出一缕缕的灰。戏台的後墙是一层薄薄的板壁,那边就是後台了。两侧各有一扇门,供上下埸用。後台是一个通间,和前台齐高,齐宽,只是略浅二、三步,就是细长的一条了。地板地,中间一条带抽屉的长桌。那些个细心的爱捣腾的孩子,从抽屉里面就可能找出一朵泛黄变脆的旧珠花、一条包头布什么的。依著那座板壁墙,放著几个戏装的箱子,上面写著一个“陈”姓,不晓得是哪个年代,也不晓得是哪个戏班留下的。後来的人也没去考究,只怕是老鼠己经在里面做了窝。後台还另有一个角门,走下几级台阶,台阶已经换成水泥的了;走下去,就到了後院。泥地,露天的厕所就在角落里,横著是 “男”竖著是“女”。对面的角落里有一棵紫莉树,可以想见,男女演员候埸时,就在这里喊几下嗓子,把脚举在墙上拔筋。这个戏台子像是没怎么动过,否则不会这么旧。唯一新的地方,是戏台正面的上方;用水泥塑了一个五角星,涂了红漆。小孩子进来玩,大多爱到这戏台子玩。
他们在戏台上,跳下跳下,互相追逐,叫喊。叫喊声在墙上激起回声。对了,还没说那顶呢!顶上横著木梁,木梁熏得发黑,想来是唱请神戏时,香火熏的。木梁上头,黑压压的,依稀可见人字型的椽子,吊著些蛛和灰串子。粱上爬了电线,安了电灯,罩著铁皮罩子。顺了梁,隔二米有一盏。过去应当是汽灯,再远些是蜡烛盏,现在有了电,当然改电灯了。这戏院子的样式多少有些像庙宇,说不定真是庙宇改的呢,所以,别看它小,却有一股森严的气氛。孩子们玩到下午四时许,光线沉下来一些,贴了门槛往里照,就看见有许多灰尘在亮亮地飞舞。埸子的四壁有些黄,涂了一层釉似的。这时候,不知怎麽就有些糁人。不定哪个顽皮孩子夸张地呼啸一声,於是,全都惊乍起来,一窝蜂地跑了出去。
解读
《富萍》中的人是个特殊的群体。这里的她们已经承袭了上海昔日的繁华和完整,却也摆脱不了偶然显露出来的乡音和不属于这个城市的某些举动。王安忆正是要描写这样一个群体,就如她早些常写的知青题材的文章一样,这个群体是她所熟悉的。六四、六五年的上海对她来说,是有感性经验的。整本书的每一章看似不经意地错开,却最终发现故事在慢慢推进。这是《富萍》的特点,表面风平浪静,可平静流淌的生活表面下面,暗流涌动。这大概也是王安忆的特点,这一系列小说中,我读到的是内在的舒缓和从容。叙述者不是强迫人物去经历一次虚拟的冒险,或者硬要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某种新的可能性。不,不是这样,叙述回归到平常的状态,它不需要刻意表现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这就是王安忆秉承的朴素的小说观念。
四.其他作品简述:
桃之夭夭
《桃之夭夭》写的是郁晓秋,一个年龄和遭际都像是王琦瑶的后代的人物。而她们之所以被王安忆不动声色却又疼爱有加地描绘,人物的没有梦想是一个原因吧。这和张爱玲的那种抹去时代痕迹、抽离政治取向、现出人性本色的挖掘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遍地枭雄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来自上海郊区贫穷的年轻人韩燕来。他来到上海干起了出租车司机的职业。韩燕来由此接触到了各种各样形形 的乘客,在自己的心里刻画出每位乘客是做什么的,有什么样的生活。枭雄不是英雄,善恶一步之遥,惊心清醒。这部王安忆最新出炉的力作,起讲述的是当今时代背景中,一个普通人,因为一次意外事件而进入异样的境地,流落江湖,过上了另类生活。题材选择与文学视角跟她以往的作品全然不同,再 次显示了王安忆在创作上的再生能力,其小说新走向令人关注。
启蒙时代
在《启蒙时代》中,王安忆以理性、精致、绵密的笔触,解剖和描述了60年代中后期,在上海,南昌、陈卓然、海鸥、阿明等几个年轻人的成长。在小说中,年轻人狂热迷恋马克思的著作和各式各样的革命理论,甚至可以大段地背诵那些欧式的华丽词句。他们燃烧 ,理想膨胀,在磨难中成长,在真实的世界里逐步去发现理想与空想的区别,从热衷于生硬的教条到自觉地去感知有温度的生活。作家保持了一贯的冷静,并没有去写风起云涌的运动,即使是描写冲突 父子之间、阶级之间,及青春的躁动、越轨,等等,也是波澜不惊,静水深流,发人深省。
流逝
《流逝》是王安忆的一篇中篇小说。故事发生在文革时的上海,描写一个资本家家庭在十年动乱中的生活境遇和变迁,主要塑造了主人公欧阳端丽的性格。写她在历史的遭遇面前,在命运浮沉之中,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角色的转型。结构紧凑,语言朴素,《流逝》获1981 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实习:白俊贤)
佳木斯治疗白斑的医院酒泉妇科医院哪家好安康白癜风好的医院
-
活下来的团购网站将是未来的骨干力量
大数据 | 2019-07-16

-
晶科电子高密度倒装芯片焊工艺欲摘封装器件
大数据 | 2019-07-15

-
用区块链物联网重新定义供应链
大数据 | 2019-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