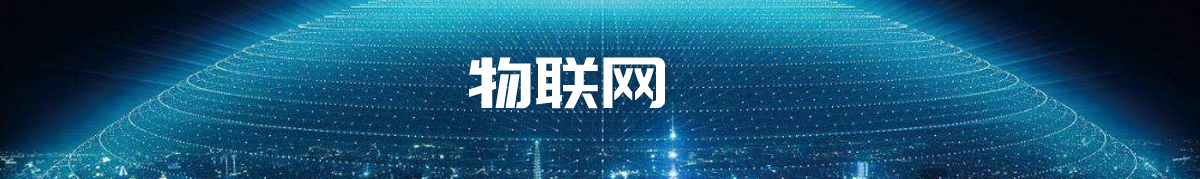藩国忆那年那地那事之苦乐求学
忆那年那地那事之苦乐求学
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求学路。
对知识的渴望是人的基本需求。知识是你在前人的基础上认知宇宙万物、自然历史、社会人文、民俗典古的有效捷径,也是掌控打开未知世界的钥匙。
我不敢说我有多么优秀,但是确实很幸运,至少我曾经努力过。
巍巍秦岭,龙耳入云。山下的小山村,左右两边都是几丈深的山前侵蚀沟,在一里外合成一条沟,像个扇形。小山村西边分别有上、下、西三个安尧村,紧靠安尧村有一座独立的“金字塔”山体,上有白皮松、侧柏,绿郁葱葱,有人说那是“尧帝陵”从村里的小路能到两个集镇,一个是东北十五里的高塘会,一个是西北十里崇凝街。
村子靠山一排房的西头有一座泥坯瓦房,那是父亲顷其毕生垒成的。我在家中排行老小,前面有三个。父亲半百时才有了我,听说我本该还有几位姐姐的,但因当时乡下没有医疗条件,加之家里条件极差,她(他)都早早折了,我是很幸运的。
虽然我生长的村地处山脚,只有十几户人家,交通不便,不灵。幼小的我却对几件事印象深刻:一件事是,有一年队里让家家都在场面子用苞谷杆搭棚子,晚上一家人挤在棚子里睡觉,后来才知道是那为了躲唐山的;再一件事是,很羡慕别人有各种式各样的纪念章和红五角星,当那天从广播中传出的噩耗,全村人发自内心地戴上了黑纱,默默地对逝去伟人,以示哀掉;第三件事是:全公社人车拉人推地修龙耳山下的牛峪水库,修水库的人们就住在我家,每当放炮时,石块乱飞,很是危险,几个命丧飞石之下,但都没有挡住人们修水库的勇气,眼看着大坝一天比一天高,拦住了峪道清澈的水,高山出平湖,水库蓄的水可浇灌东阳公社北至魏家塬大部分土地,现在因坝体、灌渠失修己不能发挥灌溉作用,但还是方圆几个村的生活水源地。
我八岁那年,背起母亲用粗布纳的书包,跟着同村一般大的孩子,翻过好深的沟,到对面的山庙小学开始求学。
刚开始学写字,习惯用左手,在老师的帮助下慢慢地改用右手了。等发了新书,如果幸运的话,能找到人家用过的水泥包装袋,用中间没有脏的牛皮纸背起来,要不就寻几张旧报纸把书包起来,能用年画包书的都是家里条件好的,即便如此到期末,书也揉成了“牛肉卷”
一个本子,正面用了用反面,没钱买新本子的,就把牛皮纸裁整齐,用针线纳起来当本子用;学习用具很少也很单一,铅笔、毛笔、油笔,最奢侈的算是父亲给我买的一个算盘和一支钢笔。
课间,男孩或用废纸折成方面宝,放在地上互相砸,谁砸翻归谁,或抛“纸飞机”看谁的飞得高飞得远,或跳斗牛,或挤在墙角相互挤取暖暖;女孩或跳绳、或踢毽子、或抓“五子”玩的也很开心。
当杏儿成熟的季节,每天早早起来,从门前的埝底,悄悄地溜到别人的杏树底下,捡起熟透了的黄澄澄的杏儿,装满书包,边走边吃去上学。
那时候的冬天特别的冷,大人们用搪瓷缸或铁水壶的壳,里面用头发和泥做成炉膛,中间棚几根粗铁丝,下面留个出灰口,放些钢炭、木炭或玉米芯引燃,提到学校里取暖。
除了发的课本外,几乎没有课外书。那时候最时兴的课外读物,就是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小人书”谁要有一本,大家都争着传着看。、杨家将岳飞传等等,看一边还想再看一边。记得上三年级时,班上有位同学,家里藏了好多“小人书”一天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他便带着我们几个去他家看了一下午的“小人书”过足了瘾,谁知第二天,班主任陈老师知道我们“逃学”了,便罚我们站在教室门口,还让那位同学把他家里所有的“小人书”都搬到学校里来,让大家看。那时候还觉得有点对不住那位同学,后来明白了班主任的用心良苦,也很敬慕那位同学的慷慨情怀。
每天翻四次沟,天嘛嘛明去,太阳下山回,幼小懦弱的我在山庙度过了三年蒙学的时光。
上四年级时,因山庙没有高年级,便不得不转到距家六七里地的涧峪口学校。
涧峪口学校位于秦岭七十二峪之一的西涧峪峪口。学校大了,学生多了,认识的多了,对事物的见解也慢慢有了自己的看法。
离家远了,只能住校。学校东南角有一座破败的土木结构的房屋,底下黄土满堂,中间棚一层木板,算是床了。刚开始还住着五、六个同学,因为条件实在差,还有老鼠,有跳蚤,气味又难闻,住了几周,大家都投亲靠友或寄宿到同学家中去了。我也住到距学校较近的同学家中。
学校没有食堂,只有一个开水灶。每到饭点,便用搪瓷缸接一缸水,拿出从家里带来的黑面或苞谷面馍泡在开水里,放点盐。就是一顿饭,一日两餐不变样。一周背两回馍,一次十八个管三天,从未间断过。冬季馍冻的瓷硬,夏季长出了毛,把发霉的扣掉,泡在开水里吃饱肚子。
每次回家背馍,一般都在周三下午,回家后吃上一顿母亲做的热饭,在家里的热炕上睡一晚。家里没有闹钟,母亲凭着看天色、听鸡鸣叫我去上学。记得一次逢月圆,母亲以为天明了,便唤我去上学,我急急忙忙起来,把昨晚的剩饭热了吃了,背上装好的一布袋馍就赶着去学校。天蓝星稀,月明如昼,四周静悄悄,鸡鸣狗叫不时入耳,踏着刚深翻耕的土地,插斜抄近路向学校赶去。等到了学校校门紧闭,没有一个人,来的早了。进不了校门,便来到学校西边的场面子,找一个“麦间垛子”就倒头又睡,一觉起来,才陆陆续续有同学来。
课外生活依然还是单调,只是把“小人书”换成了长篇小说,说岳全传、烈火金刚等。学校后面是大队部,刚开始从学校搬出来住时,我和同村一个同学,就借住在大队部理发店,每到晚上,周围的人便涌到大队唯一的一台黑白电视前,等着观看霍元甲信号时好时坏,把天线转來转去,大家看的非常过隐。
还记得在学校不远处的山口,有个买卖木头的“黑市”每到晚上,人们把从山里砍的木头,扛到这里买,一直到深夜。学校东南有蕴空山,山上有茂密的柏树林,但当木头黑市开了,未过几天,便被砍伐一空,连树根都被当地的人挖出来当材烧或点明照亮。一座座青山就这样没有了?
从四年级到七年级,我一直在这儿上学。这四年是我人生的根基,我才知道这个世界大的很,知道只有学好了考上学,才会到外面去。我一直心怀感恩,在我极为普通平凡的人生路上,总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想帮教诲。语文课贾老师在写作上,给我打开了从作文到写作的另“一扇门”懂得了作文的真正意义;代数课杨老师不仅从学业上指导,而且从生活上给了我莫大的帮助;物理课王老师把我从现实的感观认识带进了物质内在的关联理论,产生了对学习知识的不懈追求。还有许多老师和同学都是我人生阅历的财富。
八四年上八年级时,因涧峪口学校八年级撤并,我不得又转到了东阳中学。当时一起在涧峪口上七年级的同班同学,有的去高塘中学上学,有的到别处上学,各奔东西。
东阳中学距家十多里地,设有六、七、八三个年级。刚一报名,班主任孙老师对我很关心,分在他带的二班(共四个班)八年级既要学新课,又要复习备考,学习任务重。
同样要借宿,同样一星期背两回馍,同样是开水泡馍。幸有杨老师(七年级数学老师)照顾,把他家后面正住人的窑洞腾出来,让我住,冬暖夏凉,泥土气味浓郁,环境很好。从家里去学校要经过安尧、小村、核桃园等好几个村,都是土路,天晴还好,下雨天两脚沾满了粘泥,很重很沉,走同时老四应该看着老三做饭起来十分不便。途经核桃园村,据说这里曾是周朝至春秋时的古墓群,看墓的人在周围种上核桃树,便成核桃园了。
长这么大了,还从未下过高塘塬,也不知道县城在哪,是什么样子。记得有一次参加全县组织的数学竞赛,我第一次在老师的带领下进了县城,宽阔的柏油马路,整齐高大的两行梧桐树,两边是楼房。老师带我们在新华饭店门前吃油条,喝豆浆,这是我第一次“下馆子”特别是那豆浆,喝进口里怪怪地,很不习惯,却又不敢言传。那次竞赛我没有得上名次,使原来一直在所在学校班级成绩前三的我,才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更理解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
每次沿着羊肠小道回家取馍或来学校,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着在地里忙碌的人们,经历着地里的庄稼一年四季变化。一路上,我把地理、历史课本上的内容从头到尾,像过一样在脑中过一遍,对混淆或记不清的,回到学校翻开书温习一遍。其实我是很笨的,就是靠这种死记硬背的方法提高成绩的。
一年时间很短,也没有熟悉周围环境,就到了中考的日子。中考考场设在高塘中学,辛辛学子,八年的努力,终要见成果。
中考结朿后,在家等了半个月,听说参加中考的被中专录取的己体检填报志愿了,我还没有,以为自己“名落孙山”了。谁知过了几天,邻村的薛老师让人捎话,说让我去县招生办体检,在薛老师陪引下,我来到县城(这是我第二次县城)体检结束后,招生办的老师让填志愿,叮咛我一定要把渭南地区农校填第一志愿,就这样我很幸运地考上了中专。
八年在人生很短暂研究机构CRU/首席代表Wan Ling 马来西亚能够供应更多,这八年我虽然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但每一次考试总是排在前三名,很受老师和同学的夸赞,也正是这些夸赞,激励着我更加刻苦用功,总想对未知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去探探看看。八年一路走来,我曾得到了好多老师、同学、乡亲无私的帮助提携,没有他(她)们,我的人生可能会是另一条未知的路,感谢他(她)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当接到录取书时,我还在屋后的槐树上砍树枝,一不小心还把腿弄伤了。开学前,我拖着伤腿,用推土车推了一袋粮食缴到高塘粮站,就这样成了一名吃“商品粮”的。
从小没有出过远门,父母让二哥送我去上学,背起母亲为我缝的被子,扛起父亲找人给我打的桐木箱子,坐了一辆去渭南顺路的拖拉机,就这样走出了滋润我的小山村。从渭南换乘公共汽车坐到蒲城,告别了送行的,和新同学一起乘着学校接站的大卡车,来到蒲城东的孙镇一一渭南地区农业学校。
渭南农校大门是砖制的高大牌楼,对面就是杨虎臣将军的故居白杨树村,西边是渭南地区农科所,东边是农田。从大门进去是一个半园的花坛,里面有几颗雪松、棕榈、月季花,南北两条笔直的道路将院子分成三部分,西边是老师宿舍,中间一片桐树林,桐树林北是大礼堂(食堂)东边是二排一或二层窑洞,后院是男生宿舍,前院是女生宿舍。再往后边是大操场,操场的西边是三层教学楼,东边图书馆。北墙外是农学实验农场,东墙外是实习果园和苗圃地。整个校园布局美观、座落有致,与周围的村庄形成鲜明对比。
刚到学校,高年级的乡党学长,就跑前跑后地帮着报名、搬东西、送到宿舍,让我感到很亲切。我们89级有、农学、畜牧三个班,我是89班的,同学们都是来自渭南地区十二个县市,大多数来自农村的“泥腿子”都是怀惴着一样的阅历、一样的心情、一样的梦想。
前两年主要学习高中和专业基础课,后两年学专业、搞实践。少了紧张和压力,多了新鲜和好奇。细胞是那样的完美,叶绿素是那样的神奇,花是那样的美丽,种庄稼、栽果树、务蔬菜大有学问,知识的殿堂永远都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
一月三十斤饭票,二十四元菜票。男同学的饭票不够用,女同学的菜票不够用,大家互相接济着,男同学把结余的菜票给女同学,女同学把粮票给男同学,你帮我打饭、我帮你打饭,互帮互爱。长这么大了,还从没有和女同学说过话,刚开始还真有点腼腆,慢慢地敢说了,但还是不会沟通,不会讨人喜欢,至今也不善于和异性交往,大概是情商太低了的缘故吧。
每当下午没有课时,我们三两成群,披着夕阳余辉,踏着布满生命的泥土,漫步在田间小道上;有能合得来的,或坐在操场的楼板上,或坐在阅览室,或在柳林梧桐树下闭庭信步,一切都那么和谐,那么美好。
最后一年林学实习,石老师带着我们来到黄龙的石堡川林场,实习内容为采伐设计。穿行茂盛的森林中,我们区划着林班小班、用游标卡尺测量树木胸径、看着洒在林间的阳光预测着林木郁闭度,问老师那些不知名的树木花草,恨不得把从课本上学的都用上去。一次,有两个同学和大家走散了,林场工人、老师、同学们赶忙满大山的找,等回到场部,他们从另一条路回来了,大家一颗吊着的心才落地了。
四年的中专学涯转瞬即过,从少不更事步入弱冠之年,从学校步入社会,认知的空间越大,理想抱负也越大。照相师傅早早就带着设备进驻校园,大家三两一伙,或大门前、或花坛旁、或操场边、或教学楼下,到处拍照,总想把四年的记忆都留在一张张照片里。我们全班四十个同学,邀请校领导和所有代课老师,站在教学楼前,用相机对四年的学涯生活予以终结,留下了永恒的回忆。
我的记忆力确实很差,过去发生的一些记忆片段慢慢淡化,但对老师和同学的思念却愈发清晰。语文王老师、林学石老师、果树陈老师、森保权老师,班主任杨维平老师、赵磊老师、曹福利老师,还有张宏建、王满平、李玉民等等,连同四十个同学,经常在大脑里“过”
而今,滑南地区农校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四校合一,成为渭南市职业技术学院,但四年的农校生活却深深地烙在我人生的轨迹上。夜思念的老师同学,你们可好吗?
八九年农校毕业后,即入职工作,原想学习的知识将会有用武之地,但仅仅是多认识几棵植物,多知道几个原理,造林是“一年任务一季完”森林经营就是伐尽“有用之材”原来工作就这么简单。
九三年我又参加高考,以刚过线的成绩考上西北林学院。一学期上一个月的课并进行考试,上了三年,拿到了一张大专毕业证,也总算愿了大学梦。
学习是一种人生境界,更是一种追求。是对过去的挖掘,更是对未来的探究。一时一刻不学习,外面的世界已经是日新月异的了。我总是感到自己与这个世界愈来愈陌生了,好像一棵生长在乱石堆里求生存的小草,渴望着阳光的照耀、雨露的滋润。
也许是快知天命了,也许是怀旧情愫,总是想起那背着粗布书包,每天翻沟淌水,毫无目标地打开一扇又扇门,期未了拿回一张奖状,在父母在村里炫耀一番的求学时光。
趁着头脑还清醒,把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收拢起来,归置归置,为自己留下仅剩的美好回忆,我的苦乐求学生涯。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老师
老师,尊称传授文化、技术的人,泛指在某方面值得学习的人。老师一词最初指年老资深的学者,后来把教学生的人也称为“老师”。《师说》中:“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学校
学校(英语:School)教育是由专职人员和专门机构承担的有目的、有系统、有组织的,职工是教师、教工、辅导员,名称起源于民国,以影响受教育学校教育者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学校教育是与社会教育相对的概念。专指受教育者在各类学校内所接受的各种教育活动。是教育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说来,学校教育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学校主要分为四种: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学校是教师职业的活动场所,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组织环境。
巴彦淖尔白癜病医院社区获得性肺炎怎么算好金华治疗白癜风医院在哪
-
贴片晶振的小型化带动未来的科技发展经济状
区块链 | 2019-07-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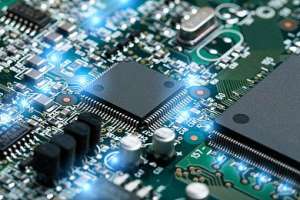
-
京东联手中电信布局农村电商
区块链 | 2019-07-15

-
物联网板块投资价值体现重点关注受益股
区块链 | 2019-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