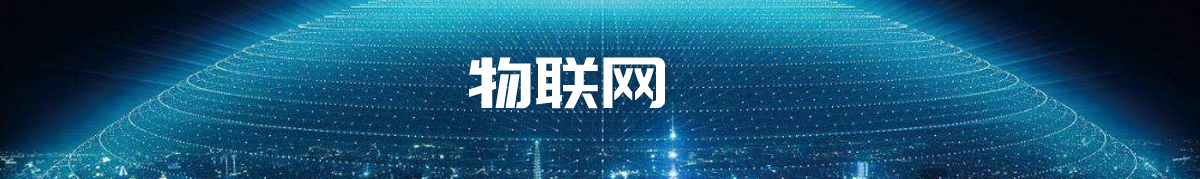大学教授质疑焚书坑儒节能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下卷),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年6月版,147 .00元。
在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最新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上、下卷)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柯马丁(MartinK ern)负责首章“早期中国文学”的写作。不同于以往“先秦两汉”的传统文学分期,柯马丁从商朝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一直写到了西汉末年刘向整理皇家书目等“经典化”活动。
此外,他在晚近出土文献和对资料深入审读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焚书坑儒”的历史真实性以及先秦时期“作者”和“书”等概念的质疑。柯马丁告诉南都,在这部力图呈现“文学文化史”的文学史新著中,他与其他十几位美国汉学家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希望借此机会,“重新思考我们对文学史的一些传统、既定的认知”。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这位德国人就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汉语。柯马丁说,自己之所以立志研究汉学造假者的手段体现得更为处心积虑。一条造假链条的曝光,与著名古典文学专家袁行霈的启蒙密不可分。留学的第二年,他每个礼拜都会到袁家,听老师给中国的博士生讲魏晋南北朝文学。“那时候我是最没什么学问的一个,像小孩一样坐着,可我还是能学到很多东西。”回德国后,柯马丁便主攻早期中国文本,在德国科隆大学拿下汉学博士学位,随后又赴美国任教。如今,柯马丁每年都会来中国进行一两次学术交流。当谈及国内早期中国的研究现状时,柯马丁却显露出几分担忧,他认为这一领域受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影响过多,“我们不是政治家,我们是做学术的,批判性精神应该是学问的基础。”
上古最难写?
南都:孙康宜说在《剑桥中国文学史》里最难写的就是你这一章“早期中国文学”。能否谈谈你的写作体会?
柯马丁:我们今天读到的所有传世的所谓“先秦著作”其实都经过了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等学者的重新整理、改写,是过滤之后“标准化”的文本。所以写这一章最大的问题是:一方面我要写一种连续性的、历史性的,有发展和过程的文学史,里面贯穿着时间的逻辑。但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因为对原始形态的了解已经受到后世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直接从早到晚写一条线,这是一种幻想《匆匆那年》以势不可挡之势拿下了4.5亿的票房。比如我要写周代的《诗经》,但实际关于周代《诗经》的资料并不多,而我们今本的《诗经》实际是《毛诗》,是某一种对《诗经》诠释的文本。如果没有《毛诗》对文字训诂的注解,就很难读懂《国风》。包括出土文献,像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竹简《孔子论诗》,那是公元前 00年左右的文本,也不是最原始的形态。所以在写作中,结构上我按照时间的线索发展,但逻辑上则需要通过文本的阐释史和接受史,由“后”往“前”讲,这一章的困难也就在这儿。
南都:你撰写的这一章里,对晚近出土的文献运用非常多。众所周知,上古时期的文献总量是很有限的。但在一部文学史的写作中,能这样充分且审慎地释读文献确实让中国的读者眼前一亮。
柯马丁:文献资料非常重要,但研究者在对待出土文献的新资料时,往往会把新资料补充进我们已知的传统文化的叙事中,或者说已存在的思想史的框架之内。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如果要真正体现或赞成这些新资料的价值,我们必须愿意接受它们与传统的概念相抵触的地方以及它所带来的新的概念。举个例子,目前90%的战国秦汉出土文献都没有对应的传世本,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正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们对先秦文本文化的了解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文本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所以新的出土文献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允许我们重新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个意义上,写作《剑桥中国文学史》不是刻意改写文学史,而是给我们一个机会,重新思考我们对文学史的一些传统、既定的认知。
南都:重新思考文学史的“元问题”,比如你对早期中国究竟是否存在“书”、“作者”这两个概念的质疑。
柯马丁:对,绝大多数的先秦两汉出土文献都没有标题,只有少数将标题写在竹简的末端背面。像《礼记》是到了汉代才按“篇”成“书”,原本都是一篇一篇的独立专论,直到最后才被编在了一起。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周易》是最大的例外。因为《周易》有一定的范围,即64卦,这是比较完整而稳定的;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出土文献谈到过它的作者,一篇也没有。比如所有的传统文献中,《民之父母》这篇文章并不存在,可是这篇文章有一部分就在《礼记·孔子闲居》,另一部分则在《孔子家语》里。由此可见,当时文本的概念没有那么稳定,没有人说我的文本是对的,你的文本是不对的,类似著作权的讨论在古代中国根本没有。正如上个问题所说,如果我们愿意注意到这一点,只能说好像作者这个概念在当时不是那么重要。以此为基础,再看西汉末年刘向编著的《别录》,大部分是按照作者来,这与出土文献呈现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概念在文本的标准化或者稳定化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字的传统
南都:你在论述中特别谈到中国早期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关系。
柯马丁: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经常用后来的现象或经验倒推前面,好像中国早期文学只是后来书面文化的更早期的版本。特别是在中国,我们经常强调文字,好像这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先秦,书面文化当然重要,但并不是整个文化的核心。没有哪一种先秦文献提及古典文本以书面形式流通传播。《左传》、《国语》中的多次引《诗》,没有哪一处提到使用的是书面文本。再比如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当时的“学”不是单纯读书,而应该是非常深刻地理解,达到背诵的程度,进而内化成我自己的东西,这是一种完整性的心性发展的自修过程。
很多人觉得一种早期文明不强调文字就是水平低,这是完全不对的。比如古希腊,荷马史诗原来也是口头文学,但却是代表了极高的文化水平。所以说,如果太过强调书面文化,不仅会误会以前的情况,而且忽略了早期中国文学的背诵、表演、礼仪等丰富的实践。
南都:说起口头文化,在中国通常会认为汉字属表意文字,但你提到“汉字是一种记号(logographs),将汉语语言书写为文字。汉字主要代表的不是观念,而是声音”。为什么?
柯马丁:有一定数量的汉字明显源于象形文字,这使得人们误认为汉字总体上是表意文字。毫无疑问,每一种文化最基础的是语言,不是文字,这是人类的自然法则。我们应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字和词是不一样的,由于绝大多数的早期汉语词汇多是单音节词,所以古典文献里的单个汉字是一个词的写法。但因为音节的极其有限,导致了大量同音字。这就是为什么汉以前人们经常用“假借字”(通假字)。反过来推,之所以用“通假字”,说明你必须要听这个字,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研究过所有的出土文献中引用《诗经》的句子,对比不同的出土版本你会明显看出重写的幅度,比如《关雎》中的“窈窕”二字,在马王堆《五行》帛书中写作“茭芍”,而在《陈风·月出》则写作“窈纠”。尽管写法不同,可只要读出来,我们马上发现是同样的词。所以我们不要低估声音的重要性,与书写活动相比起码同等重要。
南都:大家通常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更看重文字的这种传统是怎么来的呢?
柯马丁:第一从西汉末期以来,特别是通过“太学”的存在,产生了用于宫廷教学(即,“官学”)的书面文本,产生了文本稳定化、标准化的需求;第二是帝国本身的结构,从汉代起各种各样的交流都是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比如诏令、奏疏,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现象;第三,我觉得这跟中国幅员辽阔关系很大,因为方言的多样和差异性,文字不管在交流和管理上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我想这种传统与书法很有关系。汉代以后,书法变成一种艺术,变成个人性的美学的表达方式。但上述这些都是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过程,而在先秦时代,汉字显然没有那么稳定,而且,“文”的基本意义不是书面的“文章”。
应该向外人推介中国文学
南都:你对《剑桥中国文学史》在中国引进出版有何期待?
柯马丁:作为作者,我们都觉得这本书非常有用,希望中国的学者,尤其是在校读书的年轻人愿意用一个外来的角度来看自己的传统。通过这种视角,也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框架之内思考。如果我们只了解中国文学,那我们“一无所知”。因为在中国人自己看来,中国文学的一些现象很自然,但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却不尽然。正如前面所说,“作者”和“文本”在早期中国很不稳定,在周代几百年一直没有提到《诗》、《书》、《易》的作者。可是,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荷马史诗一变成了全古希腊广为人知的文本,很快就得到了“荷马”这个作者认同。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作者认同这个现象的发展过程在这两个伟大的古代文明之间有一定的出入。”
南都:在你的治学中,有没有受到世界文学甚至其他学科学者研究启发的经历?
柯马丁:当然。比如有个搞古代埃及学的德国人叫杨·艾斯曼(JanA ssm ann),他写了一本书叫《文化记忆与早期文明》(C u ltu ralMem ory an d E arlyCivilization),副标题“书写、记忆和政治想象”(W riting,R em em brance,andPolitical Im agination)。我的论文集《早期中国的书写、诗歌和文化记忆》(预计明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出版),光看书名就知道我确实受到了他有关Cultural m em ory(文化记忆)理论的影响。这个理论强调文化记忆对一个文明的认同的重要性。比如说《诗》、《书》里竭力歌颂的对文王、武王的记忆,在西周初期的铭文里却很少援引,到后期铭文才开始强调。同样,在《诗经》颂诗和《尚书》王室演说中经常提到的“天命”,在西周初期的青铜器铭文里几乎没有响应。所以这些王室演说和颂诗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失落的黄金时代的记忆,是对某个人物的想象和理想纪念,很有可能就是西周中、晚期屈原的而起来。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意识到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大学里从来没有受到多少关注。当然,这个情况有各种原因(包括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同时,我们应该承认,我们中国文学的专家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我们应该给那些搞古希腊、法国文学、俄国文学的学者解释:为什么他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文学?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不能跟周围的学术世界建立联系,恐怕中国文学研究在海外不太有前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简介:柯马丁,德国科隆大学博士,曾任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亚洲学讲座教授。学术领域涵盖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学、历史、宗教,致力于早期文本的形成、接受、经典化研究,同时对中国上古及中古诗歌的理论、美学、阐释实践有浓厚兴趣。主要著作有《早期中国的文本和仪式》、《秦始皇石刻 早期中华帝国表征中的文本与意义》等。
(实习:李万欣)
一岁宝宝腹泻怎么办产后收紧
河池专治白癜风的医院

-
管理20个城市宣布购房可以拿到补贴你能轻松买
5G | 2020-0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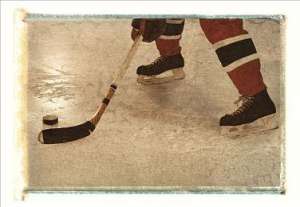
-
阿森纳英超第1巨富3董事入最新福布斯富豪
5G | 2020-07-08

-
武磊爆发给中国足球带来1最大利好留
5G | 2020-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