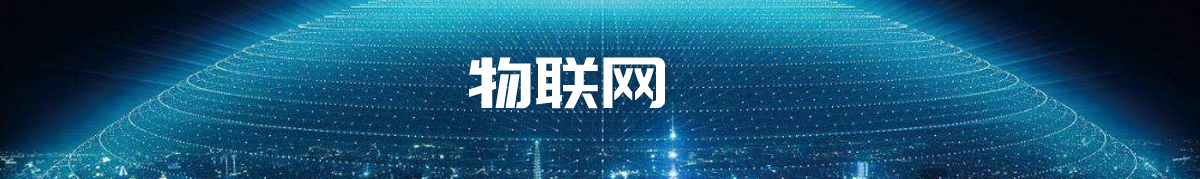即真正外部世界在心灵中的代表所改变的本我拳
超我和自我
如果自我只是被知觉系统所影响,即真正外部世界在心灵中的代表所改变的本我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要处理的局势就很简单了。但情况却是更为复杂的。
我们假定在自我之中存在着一个等级,一个自我内部的分化阶段,可以称为“自我理想”或“超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已在别处提出过了,它们依然适用。现在必须探究的新问题就是,自我的这一部分和意识的联系不如其他部分和意识的联系密切。
在这一点上,必须略微扩大一下我们的范围。我们通过假定(在那些患忧郁症的人里面),失去了的对象又在自我以内恢复原位,也就是说,对象贯注被一种认同作用所取代,这样我们就成功地解释了忧郁症的痛苦障碍。但是,在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该过程的全部意义,也不知道它的平凡和典型程度如何。自此我们开始理解,这类替代作用在肯定自我所具有的形式方面起侧重要的作用,在构成它的所谓“性格”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最初,在人一生的原始口欲期,对象贯注和认同作用无疑是很难相互区别开来的。我们只能假设,对象贯注在以后是从本我中产生的,在本我中性的偏向是作为需要而被感觉到的。在开始的时候还很不强健的自我后来就意识到了对象贯注,并且要么默认它们,要么试图通过压抑过程来防备它们。
当一个人不得不放弃一个性对象时,在他的自我中常常会发生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只能被描述为对象在自我之内的一种复位,就像在抑郁症里发生的那样,这种替换的确切性质迄今尚未为我们所知。通过这种心力内投,一种退行到口欲期的机制,可能使自我更容易放弃一个对象,或使该过程更容易成为可能。这类认同作用乃至可能是本我能够放弃其对象的唯一条件。无论如何,这个进程,特别是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是一个常常产生的进程,它说明了这个结论,即自我的性格就是被放弃的对象贯注的一种沉淀物,它包含着那些对象选择的历史。当然从一开始就必须承认,有各种程度的抵抗能力,正如在某种程度上所表明的,任何特殊人物的性情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或抵抗其性对象选择的历史的影响。在有过屡次恋爱经历的女人中,似乎并不难在其性情特质中发现其对象贯注的痕迹。我们也必须斟酌同时发生的对象贯注和认同作用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对象被放弃之前,它还会产生性格上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性情的变化将能从对象关系中幸存下来,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保存它。
从另一种观点来看,也许可以说,1个性对象选择的这种向自我的变化也是自我借以取得对本我的控制,并加深和它的联系的一种方法。确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默认本我的经验为代价的。当自我假定对象的特点时,可以这么说,它把自己作为一个恋爱对象强加给本我,并试图赔偿该对象的损失。它说:“瞧,我这么像那个对象,你也可以爱我。”
这样产生的从对象力比多向自恋力比多的转变,明显指的是对性目的的放弃,即一种失 化的过程,所以,它是一种升华作用。的确,这个问题应当得到认真的斟酌,即是不是为升华作用所走的普遍道路,是否一切升华作用都不是由于自我的媒介作用而产生的,自我通过把性对象力比多转变为自恋力比多,然后,或许继续给自我提供另一个目的。以后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其他本能变化,是不是也有可能不是由这类转变造成的。例如,是否这类转变不会造成已融会在一起的各种本能又被分解。
虽然这有点离题,但是,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把注意力扩展到注意自我的对象——认同作用。如果这些认同作用占了上风,并且变得为数过多、过分强大,且互不相容,那么取得病理学的成果将为期不远了。由于不同的认同作用被抵抗相互隔断,可能会引发自我的分裂,也许所谓多重人格这种情况的秘密就是各种认同作用轮番占有意识。即便事情不至于如此,在支离破碎的自我的几种认同作用之间存在着冲突问题,这些冲突毕竟是不能描写成完全病理学的。
但是,不论对这种被放弃的对象贯注的影响进行抵抗的性格能力,在数年之后其结果可能是什么,童年最早期的第一次认同作用的影响将是深刻而持久的。这就把我们领回到自我理想的起源。因为在自我理想的背后隐藏着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认同作用(即父亲认同的作用),这是在每个人的幼年期就曾发生的。这显然并不是最初对象贯注的结果,这是一种直接的、即刻的认同作用,比任何对象都早。但是,属于最早的 期,并且与父母有关的这种对象选择,正常说来,仿佛会在被讨论的那种认同作用中发现其结果,因此而强化前一种认同作用。然而,全部问题是如此复杂,有必要更细致地探究它。问题的扑朔迷离归之于两种因素:俄狄浦斯情结的三角特点和每一个人身体上的雌雄同体。
男孩子的情况可以简单地叙述如下。在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小男孩就发展了对他母亲的一种对象贯注,它最初和母亲的 有关,是在所依赖的原型上最早的对象选择的例子,男孩子用以父亲认同的方法来对付他的父亲。这两种关系一度同时存在,直到对母亲的性欲望变得更加强烈,而把父亲看做是他的障碍,这就引发俄狄浦斯情结。于是以父亲认同的作用就带上了一种敌对色采,并且变成了驱逐父亲以取代他对母亲的位置。此后和父亲的关系就有了心理上的矛盾,在认同作用中这类内在的矛盾心理好像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对父亲的矛盾态度和对母亲的那种充满纯洁深情的对象关系,构成了男孩子身上简单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
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退化,对母亲的对象贯注就必须被放弃。它的位置可被这两种情况之一所取代:要末与母亲认同,要末加强与父亲认同的作用。我们习惯上认为后1结果更为正常,它允许把对母亲的深情关系看做是保存的一部分。这样,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将加强男孩性情中的男子气。小女孩身上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以完全类似的方式,可能就是加强以其母亲认同的作用——这种结果将以女子气表现儿童的性格。
由于这些认同作用并不包括把被放弃的对象吸收到自我中去,因此,它们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东西。但是这种二择一的结果也可能出现,在女孩子身上比在男孩子身上更容易观察到。分析常常表明,当一个小姑娘不再把她的父亲看做恋爱对象以后,就把她的男子气突显出来,并且与其父亲认同,即与失去的对象认同,来代替与其母亲认同。这将明显地依赖于她的素质中男子气是不是足够强烈,而不管它可能是由什么构成的。
由此看来,在两种性别中,男性素质和女性素质的相对强度,是肯定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将是一种以父亲认同还是以母亲认同的作用。这是雌雄同体借以取代后来产生了变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方式之一。另一种方式更为重要。因为人们得到的印象是,简单的俄狄浦斯情结根本不是它最普遍的情势,而是代表一种简化或图式化。的确,这对实际目的来讲常常是非常恰当的。更深入的研究通常能揭露更全面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情结是两重的(消极的和积极的),并且归之于最初在童年表现出来的那种雌雄同体。也就是说,一个男孩子不仅对其父亲有一种矛盾态度,对其母亲有一种深情的对象选择;而且他还同时像一个女孩那样,对他的父亲表示出一种深情的女性态度,对母亲表示出相应的敌意和妒忌。正是这类由雌雄同体所带来的复杂因素使人难以取得一种与最早的对象——选择和认同作用有联系的清楚的事实观念,而且更难以明白易懂地描写它们,甚至可能把在与父母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完全归咎于雌雄同体,如我刚才所说,它不是从竞争和认同作用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看来,特别是触及神经官能症患者时,假定存在着完全俄狄浦斯情结是可取的,精神分析的经验则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它的构成成份总要有一方或另外一方的消失,除那些只有依稀可辨的痕迹之外,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系列,即一端是正常的、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另外一端则是倒置的、消极的俄狄浦斯情结,而其中间的成份将展现两个成分中占优势的那种完全的类型。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分解,它所包含的四种倾向将以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组织起来,以产生一种父亲认同作用和母亲认同作用。父亲认同作用将保存原来属于积极情结的对母亲的对象——关系,同时将取代之前属于颠倒情结的对父亲的对象——关系;母亲认同作用除在细节上做必要修正外,将同样是真实的。任何人身上两种认同作用的相对强度总要在他身上反映出两种性的素质中的某一种优势。
受俄狄浦斯情结安排的 期的广泛普遍的结果,被看作是在自我中形成的一种沉淀物,是由以某种方式结合到一起的这两种认同作用构成的。自我的这类变化保存着它的特殊地位,它以一种自我理想或超我的形式与自我的其他成份构成对比。
但是,超我不仅是被本我的最早的对象选择所遗留下来的一种沉淀物,它也代表反对那些选择的一种能量反向作用。它和自我的关系其实不限于这条规则,即“你应当如此如此(就像你的父亲那样)”;它也包括这条禁律,即“你绝不能如此如此(就像你的父亲那样)”,就是说,你不能做他所做的一切,有许多事情是他的特权。自我理想的这种两面性是从这个事实中取得的,即自我理想有对俄狄浦斯情结施加压抑作用的任务。显然,压抑俄狄浦斯情结并非易事。父亲,特别是父亲被看作是实现俄狄浦斯愿望的障碍,这样,儿童的自我便取得了强化,在自身之内建立这个一样的障碍以帮助其进行压抑。做到这一点的气力可以说是从父亲那里借来的,这种出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行动。超我保持着父亲的性格,当俄狄浦斯情结愈强烈,并且愈迅速地屈从于压抑时,超我对自我的安排,愈到后来就愈加严厉——以良知的形式或者以一种潜意识负罪感的情势出现。我在后面将提出一条以这类方式支配权利的根源的建议。这个本源,就是以一种绝对必要的情势表现出来的其强制性情的根源。
如果我们再次考虑一下已经描写过的超我的本源,将它看作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的结果,一个是生物因素,另一个是历史因素,即在一个人身上长时间存在的童年期的无能和依赖性,和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事实和我们已经表明的那种压抑,都和力比多潜伏期的发展中断有关,而且也和人的性生活活动的两重发动能力有关。根据一个精神分析学的假定,人们最近提到的那个对人类来说仿佛很独特的现象,是冰河时期文化发展的一个遗产。因而我们发现,超我从自我中分化出来无非是个机遇问题:它代表着个人发展和种族发展中最重要的特点。的确,由于它永久反应着父母的影响,因此,它把其根源归之于这些因素的永远存在。
精神分析一再受到指责,说它不顾人类本性中较高级的、道德的、精神的方面。这种指责在历史学和方法论这两方面都是不公正的。首先,我们从一开始就有把进行压抑的功能归之于自我中道德的和美学的倾向;其次,一般人都谢绝承认精神分析研究能产生一种全面、完善的理论结构,就像一种现成的哲学体系那样。但不得不通过对正常的和变态现象的分析解剖,沿着通往理解心理的错综复杂的道路,一步一步地找到它的前途。只要研究心理上这个被压抑的部分是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必要对存在着更高级的心理生命感到不安和担心。但是,既然我们已着手进行自我分析,我们就可以对所有那些道德感受到震惊的人,和那些抱怨说人体中一定有某种更高级性质的人做出回答。我们可以说:“千真万确,在这个自我理想或超我中,确有那种更高级性质,它是我们和父母关系的代表,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这些更高级性质了。我们既羡慕这些高级性质又害怕它们,后来把它们纳入到我们自身中来了。”
因此,自我理想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因而也表示在本我中力比多所体验到的、最有力的冲动和最重要的变化。通过建立这个自我理想,自我掌握了它的俄狄浦斯情结,同时使自己处于本我的安排之下。鉴于自我主要是外部世界的代表,是现实的代表,而超我则和它形成对照,是内部世界的代表,是本我的代表。自我和理想之间的冲突,正如现在我们准备发现的那样,将最终反映真实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之间、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的这种对立。
通过理想的形成、生物的发展和人类种族,所经历的变迁遗留在本我中的一切痕迹被自我接受过来,并在每个人身上又由自我重新体验了1遍。由于它所构成的方式,自我理想和每一个人在种系发生上的天赋——他的古代遗产——有很多联系点。因此,正是这类我们每个人心理生活中最深层的东西,通过理想的构成才变成我们所评价的人类心灵中最高级的东西。试图给自我理想定位,乃至在已经给自我肯定了位置的意义上,或试图对自我理想进行任何类比,都只能是白费力气。
不言而喻,自我理想在一切方面都符合我们所期望的人类的更高级性质。它是一种代替做父亲的渴望。自我理想包含着一切宗教都由此发展而来的萌芽。宣布自我不符合其理想的这个自我判断,使宗教信仰者产生了一种以证明其渴望的无用感。随着儿童的长大,父亲的作用就由教师或其他权威人士继续承担下去。他们把指令权和禁律权都交给了自我理想,并且继续以良心的形式发挥对道德的稽查作用。在良知的要求和自我的实际成就之间的紧张,是作为一种负罪感被体验到的。社会情感就建立在以他人自居且和它们一样的自我理想的基点上。
宗教、道德和社会感——人类最高级的东西的主要成分,最初是同一个东西。根据我在《图腾与忌讳》中提出的假定,它们的获得从种系产生上讲出自恋父情结,即在掌握俄狄浦斯情结本身的实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宗教和道德的限制,和为了克服由此而保留在年轻一代成员之间的社会情感。在发展所有这些道德的东西时,仿佛男性居领先地位,然后通过交叉遗传转移给女性。乃至在今天,社会情感也是在对其兄弟姐妹的妒忌和竞争的冲动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敌意不能令人满意,便发展了一种对从前对手的认同作用。研究同性恋的温和情况进一步证实了这类怀疑,即认同作用代替了继敌意、攻击性态度之后的深情的对象选择。
然而,随着种系产生的提出,新的问题产生了,使人们想从这里沮丧地畏缩回去。但是,这是毫无益处的,由于我们必须做出尝试——虽然畏惧它将揭露我们建立起来的整个结构的不适当,问题在于:究竟是哪个,是原始人的自我还是他的本我,在它们的初期就从恋父情结中获得了宗教和道德?假如是他的自我,为什么我们不略述一下这些被自我所遗传的东西呢?假如是他的本我,它是怎样和本我的性质相一致的呢?或者说,我们把自我、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分化带回到这样早的时期是错误的吗?难道我们不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关于自我里面的这1过程的整个概念对理解种系发生毫无帮助,也不能应用于它吗?
让我们先回答容易回答的问题。自我和本我的化分不但要归因于原始人,乃至要归因于更简单的生命情势,由于这是外界影响的必定表示。根据我们的假设,超我实际上起源于致使图腾崇拜的经验。到底是自我还是本我体验到,并且取得了这些东西的问题,不久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了。思考立刻向我们表明,除自我之外,没有甚么外部变化能够被本我所体验到,自我是外部世界通往本我的代表。因此,根据自我来谈论直接遗传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里,实际个体和种系概念之间的鸿沟才变得愈加明显起来。另外,人们一定不要把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差异看得过分严重,但也不要忘记,自我基本上是经过特殊分化的本我的一部分。自我的经验似乎从一开始就遗留给了后代,但是,当这些经验足够常常地重复,并在许多代人身上有了足够的强度以后,就转移到本我的经验中去了,即成为遗传所保留下来的那种痕迹。因此,在能被遗传的本我中,贮存着由无数自我所致使的存在遗址,并且当自我形成它的脱出本我的超我时,它也许只是恢复已经逝去的自我的形象,并且保证它们的复活。
超我借以产生的方式解释了自我和本我的对象——贯注的初期冲突是怎样得以继续进行,并和其继承者(超我)继续发生冲突的。假设自我在掌握俄狄浦斯情结方面没有获得成功,那么,从本我产生的俄狄浦斯情结的精力贯注,将在自我理想的反向作用中找到一种发泄口。在理想和这些潜意识的本能偏向之间可能发生的大量交往说明,理想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潜意识的,自我是进不去的。在心理的最深层曾经剧烈进行的斗争,并未因迅速的升华作用和认同作用而结束,现在是在更高层次的领域内进行着,就像在科尔巴赫的油画《汉斯之战》中一样,是在天上解决争端的。
【注】:本文选自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弗洛伊德说梦境与意识》,编译:高适。
(:王怡婷)
常州治疗子宫内膜炎费用肾阳虚食疗养生的方法
怀化比较好的妇科医院

-
管理20个城市宣布购房可以拿到补贴你能轻松买
5G | 2020-0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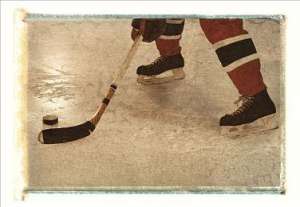
-
阿森纳英超第1巨富3董事入最新福布斯富豪
5G | 2020-07-08

-
武磊爆发给中国足球带来1最大利好留
5G | 2020-06-30